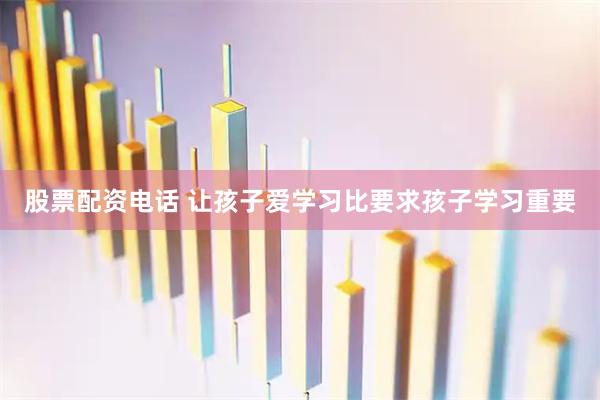图片股票配资电话股票配资电话
安理会实践的规范目的:谁是“保护责任”履行过程中的“有能力者”?
图片
作者:Jason Ralph,利兹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昆士兰大学国际关系学名誉教授,研究兴趣包括英国学派、建构主义和实用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保护责任及联合国与全球治理;Jess Gifkins,悉尼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高级讲师,昆士兰大学亚太保护责任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研究兴趣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的合法性实践、保护责任及大规模暴行的早期预警。本文曾获《欧洲国际关系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17年最佳论文奖。
来源:Jason Ralph and Jess Gifkins, “The Purpose of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Practice: Contesting Competence Claims in the Normative Context Created by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3, No. 3, 2017, pp. 630-653.
导读
国际社会应通过联合国安理会采取集体行动,保护人民免遭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种族清洗和灭绝种族罪之害的理念仍然是一种规范性的愿望。然而,有证据表明,这一愿望并非完全是乌托邦。近几十年来,安理会不仅有可能对大规模暴力事件做出反应,而且有可能采取旨在保护平民的强硬措施。然而,同样明显的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不总是采取集体行动。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对安理会实践的研究能够如何为回答“集体行动为什么会失败”这一问题作出贡献。更具体地说,本文试图揭示近年来国际关系学中的“实践转向”能够如何为研究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2P)规范的实施过程提供灵感。
国际关系的实践理论以实践的定义为中心,即“内嵌在特定组织环境中的模式化行动”的 “能力表现(competent performance)”。作者认为,这种受布迪厄影响的实践理论可以为安理会和保护责任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它突出了一系列往往处于分析背景中的问题,例如安理会的重要非正式实践“执笔者(pen-holding)”。然而,作者提出,实践理论目前的贡献可能受限于它“与规范理论处于不同的分析层面”的固有观点。脱离R2P的规范背景来考虑实践有可能导致对“能力(competence)”的误用,并将可能不符合规范目的的实践具体化。
受布迪厄影响的国际关系实践理论强调日常实践的前反思性(pre-reflexivity),其他学者对实践的定义则关注外交官对实现规范性目标做出最好的实际判断。基于实用主义的更广泛理解,这些对实践的替代定义坚持反思性和审慎性,从而使日常实践不会成为行使良好判断力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践就是Mervyn Frost所说的“道德能力”问题,而这正是保护责任对联合国外交官的规范性要求。在 R2P 所创造的规范背景下开展工作需要外交官将他们所认为的对大规模暴行的最适当回应与维持作为R2P核心伦理基础的普世主义(cosmopolitanism)意识相协调。本文的论点是,在国家对R2P的承诺所创造的规范背景下,伦理能力要求安理会外交官进行批判性的自我反思,这样日常实践才不会成为制定集体应对措施的不必要障碍。国际关系实践理论可以根据更广泛的道德标准而非特定的专业标准来衡量“能力”。
国际社会对利比亚的干预
Adler-Nissen和Pouliot在他们关于2011年利比亚干预的文章中,通过展示他们所谓的 “实践中产生的内生资源——社会技能或竞争力”中存在的“涌现权力”,将实践理论应用于国际关系。当国家的外交官在“削弱对手的类似主张”的同时培养出能力和技巧的声誉时,国家就能发挥影响力。因此,安理会成员之间的实践是“能力之争(struggle for competence)”。他们具体论点是,英国和法国外交官能够主导联合国对利比亚危机的反应,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如何应对问题上一定有最好的想法,而是因为他们在安理会的日常实践中特别有能力;他们对外交官玩的游戏有特别好的“感觉”。
本文作者对内部人士的访谈证实了Adler-Nissen和Pouliot的一些观点,特别是英法外交官为通过第1970和1973号决议而加速外交进程的娴熟手法。然而,他们对这些做法的分析似乎存在一些混淆,这对规范性研究有重大影响。这种混淆源于未能澄清外交官的目的:将安理会谈判表述为权力之争,这意味着这些决议的实质内容和更广泛的规范背景无足轻重。为了突出实践中的权力斗争,实践的规范性目的被推到了幕后。让利比亚叛逃的外交官在安理会发言而扭曲联合国程序的做法被认为是英法“能力之争”的一部分,而不是为保护利比亚人民而采取的有用举措;接受黎巴嫩的建议,在决议中加入“没有外国占领”的内容,被视为一种“狡猾的妥协”而不是为了确保集体反应。
Adler-Nissen和Pouliot的核心观点,即对利比亚的干预不是为了某件事(保护责任),而是为了某个人(英法外交官),存在重要的漏洞。例如,为什么德国未能投票赞成第1973号决议会被说成是德国的无能而不是英法的无能?这里存在一种混淆的危险,即德国对决议的实质和规范目的存在怀疑,而不是外交实践的无能。由此,将政策立场贴上“无能”的标签就是一种规范性的举动,而这将使实践理论无法实现其宣称的客观性。
安理会实践的规范目的
Adler-Nissen和Pouliot认为,实践确实会通过能力竞争过程发生变化。他们提出了一种温和的竞争形式,即“参与者接受能力标准,但对自己和他人在能力标准中的分类方式提出质疑”和一种激烈的竞争形式,即“不仅涉及另一成员的能力,还涉及对能力定义的质疑”。在后一种情况下,成功的竞争形式“不仅改变了参与者之间的相对地位,也改变了游戏本身”。这一理解的问题在于,它没有说明行为主体为何会质疑能力的定义。只要实践理论被认为是在与规范理论不同的分析层面上运作,它就无法回答这一问题。
然而, R2P通常被视为对主权相关实践的挑战,同时也是对安理会实践的挑战。它是一种“厚重”的争议形式,要求在寻求实现两个可能相互竞争的目标(即人类保护和国家主权)之间寻求平衡。因此,保护责任的实践要求Frost所说的“道德能力”:作为两种“全球实践”(即“全球公民社会”和“主权国家社会”)的参与者,联合国外交官必须“关注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紧张和冲突”。他总结说,这里所需的“道德能力”“是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实现道德一致性的能力,包括思考并实施实际调整的意愿和能力”。
因此,布迪厄影响下的实践定义有了另一种选择,它使我们能够在规范背景下评估安理会的外交实践。Frost和Lechner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指出,实践是一种语言游戏,它有助于构成国际社会的规则。从这个角度看,国际实践判断的外部目的更加明确:它是构建和维护反映国际社会价值观的规则。在这一背景下,判断仍是重点,借鉴Frost先前的概念,实践理论应评估外交官如何“协调”整个国际社会的多元价值观。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外交表现是国家所承诺的规范背景下的道德能力或实践推理问题,而不仅仅是外交习惯背景下的专业能力问题。更具体地说,在国家对保护责任的承诺所创造的规范背景下,道德能力要求以建立和维护普世主义意识的方式应对大规模暴行。
从这一视角评估安理会外交官的表现并不一定会得出与Adler-Nissen和Pouliot不同的结论。英法外交官在他们对保护责任的承诺所创造的背景下就如何应对利比亚局势达成了可行的共识,但作者的论点是,这种共识是薄弱的、不可持续的。首先,任何同意采取军事行动保卫班加西的国家都极难以北约领导的军事行动太过分为由撤回对第1973号决议的支持。鉴于暴行的威胁迫在眉睫,怀疑论者在外交上几乎没有回旋余地。其次,当南非等国寻求对军事方案的执行提出意见时,却被明确告知他们的努力不受欢迎。例如,一位外交官报告说,法国警告前往利比亚的调解小组不要前往,因为轰炸即将开始。
根据Adler-Nissen和Pouliot的分析,人们可能会认为这再次证明了P3(英国、法国、美国,The Permanent 3)的能力。然而,如果我们重新引入集体决策对R2P规范实施的重要性,那么对倾向于政权更迭的第1973号决议的解释就会使这一分析变得不同。事实上,随着军事行动超出预期,安理会成员的疏远感也在加剧。也许最有问题的举措是在2011年3月29日的伦敦会议上成立的由P3主导的利比亚联络小组。虽然中俄受到了邀请,但显然他们不会参加,因为他们认为该小组破坏了安理会,且正在努力实现政权更迭——对他们来说,这超出了保护平民的范畴。P3从未考虑过重返安理会以延续任务的合法性,因为这会导致僵局。P3外交官承认,自第1973号决议通过以来,对P3的政治支持发生了变化,但他们却坚持认为北约执行任务的方式是正确的,这似乎是放弃了协调人类保护和集体决策的努力。R2P要求在安理会培养集体的普世主义意识。在这方面,P3的外交能力被误导了:他们没有充分重视俄罗斯和中国的意见,这对安理会集体意识的延续不无影响。
因此,这里的论点是,保护责任规范及其对安理会防止暴行的集体责任的强调,确实对“保守的多边外交世界”及相应的称职外交的定义构成了挑战。在这一新的规范背景下,称职的外交是要培养和维持安全理事会基于保护责任的集体意识。这不仅仅是指在某一特定情况下对议程发号施令,以追求自己所偏好的实质性结果。这一更高的能力标准隐含着一个潜在的困境:如果为促进集体反应而做出的妥协产生了不符合保护责任规范的结果怎么办?在这一背景下采取行动的提示我们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判断的重要性,同时需要对保护责任的含义进行更广泛的反思,从而使其实践不会被看似无法解决的两难问题所束缚。
安理会实践与叙利亚危机
俄罗斯和中国显然在否决P3关于叙利亚的决议草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P3的外交实践是称职的。仔细研究P3在起草这些决议时的判断有助于阐明一个核心观点:一旦 R2P规范回到分析视野中,Adler-Nissen和Pouliot用来评估安理会实践的能力定义就不完整了。将重点放在P3对R2P的承诺所创造的规范背景上,就会使西方对政权更迭的坚持成为问题,正如在利比亚问题上所做的那样,P3主张“阿萨德必须下台”并非没有道理。然而,这一论点未能充分考虑到使其无法实现的各种因素。P3呼吁阿萨德下台的做法缺乏对实际的正确判断,这可能有助于塑造西方国家“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形象,但也导致安理会未能就保护叙利亚人民的实际方法达成一致。
无论是从对俄罗斯外交官言论的文本分析,还是从作者的访谈数据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P3在利比亚问题上的做法及其在安理会内部引起的挫败感使得俄罗斯更容易投出否决票。中国与俄罗斯一起投了反对票;巴西、印度、黎巴嫩和南非投了弃权票。反对的理由是不应允许P3在安理会重蹈在利比亚问题上的覆辙。访谈数据表明,P3内部有一种观点:围绕第1970号和第1973号决议的外交实践可以而且应该重演。从这个角度看,中俄担心“他们看到了与利比亚决议谈判过程中相同的方法”及安理会“正在变成政权更迭的机器”的观点是正确的。
在此背景下,任何将人类保护与政权更迭挂钩的 P3 建议都不符合R2P的规范要求,因为它无法与该规范坚持的通过安理会协调应对大规模暴行的要求相一致。因此,P3外交官对什么是实际可行的判断有误。此外,有理由认为,P3外交官们更感兴趣的是占据道德制高点,而不是通过谈判做出集体回应。在决议被否决之后,美国表示:“安理会的几个成员国继续阻止我们实现我们在此的唯一目的,这让我们感到厌恶。”英国称“对俄罗斯和中国决定否决一项本可达成共识的决议感到震惊”,并继续称中俄“未能履行其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责任”。然而,如果这些言论的目的是改变中俄对阿萨德政权的维护,那么这一策略失败了。如果保护叙利亚人民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安全理事会开展工作,那么通过羞辱关键成员来疏远他们就不是审慎的外交策略。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保护责任需要一种替代方法来协调人类保护和集体行动。所谓的“人道主义轨道(humanitarian track)”提供了这样一种选择。虽然这不是安理会履行其保护责任的理想方式,但争议较少,因此比政权更迭更容易实现。例如,当英国和摩洛哥在2012年2月提出决议草案呼吁人道主义准入时,中俄都没有提出抗议。两个因素促进了这些决议的谈判:政治局势的变化和执笔者(penholder)的更换。首先,到2013年9月,P3已经决定不再考虑“利比亚式”的方案,这使得安理会内部的气氛明显改善。其次,执笔者从P3更换为了三个非常任理事国:澳大利亚、卢森堡和约旦(E3),这使安理会能够在这一变化了的政治背景下采取行动。这进一步证明,一旦保护责任规范被重新纳入分析视野,我们就能够挑战“P3是最有能力的实践者”这一固有观点。
P3对E3所倡导的人道主义轨道表示了担忧,认为其会妨碍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上得以恢复的政治轨道。然而,E3双边会谈代表的谈判技巧证明他们能够在这一轨道上游刃有余。事实上,他们能够说中俄,使其相信关于人道主义准入的决议并非“利比亚式”战略的一部分。同时,一位受访者将E3描述为P3的“绝佳合作伙伴”。约旦的加入也很重要,其不仅是安理会中的阿拉伯代表,而且还收容了许多叙利亚难民,承担了许多人道主义负担。这为澳大利亚和卢森堡提出的论点增添了道义分量和合法性,阿拉伯国家的受访者证实这一点。受访者认为E3的领导对于克服P3与中俄之间的现实分歧非常重要。从这一角度看,如果执笔者仍停留在P3和中俄之间,决议就不会获得通过。
2014年7月,E3推动通过了另一项决议,授权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在未经叙利亚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使用跨越冲突线和边境口岸的路线。令一些安理会内部人士感到惊讶的是中俄并未反对本项决议。原因似乎是E3只关注人道主义,虽然决议对叙利亚主权提出了条件,但其原因却与政治干预无关;决议提及政治局势只是为了强调 “如果危机得不到政治解决,人道主义局势将继续进一步恶化”。换句话说,安理会通过了一项与保护责任相适应的决议,但这只是因为它将人道主义与政权更迭脱钩,而且 E3(而非P3)的领导促进了以务实而非意识形态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一结论再次对Adler-Nissen和Pouliot关于安理会实践的论述中提出的能力归属提出了质疑。
结语
本文的分析表明,在当前安理会的实践中,履行保护责任的能力仍然存在很大障碍。Adler-Nissen和Pouliot在没有规范框架的情况下分析了安理会在利比亚问题上的实践并得出了“P3”是最有能力的实践者的结论,而本文所加入的R2P的规范视角则对这一结论提出了挑战。保护责任的承诺意味着应根据该规范所包含的道德标准来评估他们的实践。以保护责任的规范承诺为出发点,能力的标准从实现预期目标的能力转变为培养和维持保护平民的集体意识的能力。而由P3主导的草案起草等过程则加剧了形成集体意识和方法的难度。这些排斥性做法对安理会如何应对具体案例产生了实际影响。当前国际关系学的“实践转向”存在着这样一种风险,即受布迪厄影响的理论中会简单地将类似于“执笔者”的做法重新整合,并对与之相伴的能力不加质疑。本文采用的实践概念减轻了这一风险。它将外交能力等同于协调各种规范性承诺的实践判断。
译者:吴文博,国政学人编译员,剑桥大学政治学与国际研究硕士生。
拓展阅读:实践中的权力:国际社会干预利比亚背后的多边外交进程| 国政学人校对 | 饶趋 张学玉
审核 | 李源
排版 | 赵弘宇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图片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尚美配资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河南配资公司 《用之取财》民间孤本择日,此书有趋吉避凶,在祭祀、求嗣、结婚、嫁娶、搬移、修宅、安葬等事之前都会进行择良辰吉日。否则必会造成不良后果。内含各种择日内容:水痕日,合婚定局,九天逢开起例,嫁娶忌宿,嫁娶忌日周堂例,男女岁星定局,鸡走煞,行嫁白虎周堂例,孤辰寡宿 忌婚嫁,罗帐白虎煞 忌安床,...
-
正规长沙配资平台 《燕云十六声》帷帽女隐藏后续内容介绍
-
实体配资公司 被彭德怀打的落花流水的麦克阿瑟,为什么会被解职?不仅因为战败
-
股票配资电话 勇士球星德雷蒙德·格林对主帅史蒂夫·科尔被驱逐事件发表了深刻见解
-
股票配资电话 科大讯飞:2025年12月16日科大讯飞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